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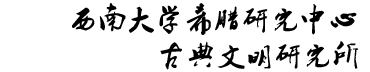
| 晏绍祥: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邦政治中的平等趋向 |
| (发布日期: 2016-05-09 10:04:44 阅读:次) |
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邦政治中的平等趋向
晏绍祥
摘 要:本文从希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平等”入手,讨论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邦政治中走向平等的一般趋势。其时来库古和梭伦偏爱的“优良秩序”已经不能满足希腊民众一般的要求。在萨摩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和库列涅等地的变革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追求平等的趋势。但平等最为充分的体现,体现在雅典经克里斯提尼改革创立的政治和制度之中。通过重组阿提卡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克里斯提尼不仅在雅典实现了民众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且实现了公民对国家管理的平等参与。克里斯提尼改革本身可能就是公民平等的结果。他所创立的制度,也因此成为民主政治的原始版本。 关键词:优良秩序 平等 克里斯提尼改革 政治参与 转载自:《古典学评论》第1辑 “平等”(isonomia)是古典时代希腊城邦主要的政治口号之一。学者们公认,它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是民主政治的前奏。西方学者对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发展多有讨论,但中国学者对它似乎仍不够了解,相关论著中也缺乏具体讨论。本文期望结合公元前6世纪希腊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对这个概念的起源及其基本含义做一个基本介绍。 从“优良秩序”到“平等” 古风时代前期,希腊城邦政治的基本走向,是“优良秩序”(eunomia)。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与雅典的梭伦改革,口号都是“优良秩序”。虽然在斯巴达,优良秩序更多地与说服、远见和谨慎联系在一起,强调顺从和服从,以及国家对公民个人的绝对强势地位,“‘优良秩序’作为‘说服’的姊妹、‘远见’的女儿,既在个人也在国家身上占据了优势,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如果像后来一样,当时是‘万物之主风俗’统治着斯巴达,则‘优良秩序’就是顺从和服从这个风俗,其中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1]然而,它终归解决了斯巴达公民基本的土地和对政治的参与问题,让斯巴达从此赢得了稳定。而在雅典的梭伦改革中,优良秩序不仅代表着正义,更代表着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对梭伦而言,城邦的命运寄托于公民的作为和命运,[2]“对城邦任何成员的伤害,间接地,但同样确定地伤害了城邦所有的成员,因为尽管最初的不公仅仅及于一人或者少数人,但对共同幸福的最终果报将损害所有人的幸福,因此,任何人的冤屈,是所有人的事情。”[3]因此,与斯巴达等城邦要求于公民绝对服从国家不同,梭伦体制之下,城邦通过授予公民必要的权利,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来确保城邦正义的实现。耶格尔曾经认为,梭伦的改革,创造了雅典的政治文化。[4]而梭伦的政治文化,正是从公民个体的命运将影响到所有人,因此所有人都需要享有某些权利,以帮助受到不公待遇的他人为前提。具体的做法,则是鼓励公民参与国家治理,以公民全体为依托,保护个人不受伤害,进而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司法上诉权等渠道,把雅典公民变成雅典城邦和公民个人命运的掌握者。[5] 虽然梭伦已经认识到,城邦是公民的城邦,公民个人的命运与城邦的命运息息相关,并据此鼓励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把国家交托于公民。通过取消债务,废止债务奴役,承认公民土地私有权,把占有土地与公民资格联系起来等措施,梭伦界定了雅典公民资格,把公民与外侨、奴隶等非公民团体清晰地区分开来。[6]但在梭伦等级化的优良秩序体制下,富人仍然把持着雅典国家的主要权力,典型表现是高级官职限于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公民,第三等级的公民只能担任低级官职,而占人口多数的第四等级,只享有最为基本的公民权,例如出席公民大会,参与审判等。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照梭伦当初立法的本旨,赋予平民的实权是有限度的,他所规定的民权仅仅是选举行政人员并检查哪些行政人员有无失职之处;这些都是平民应有的权利,他们倘使没有这些权利,就同非公民的奴隶无异,这就可能转而为城邦政府的仇敌了。他规定一切职官都须在著名人物(才德)和小康以上的家庭(资产)中选任;必须是‘五百斗级’或所谓‘双牛级’(即第三级)或骑士级才有当执政人员的被选举权。第四级,即佣工,是不容许担任任何官职的。”[7]所以,在整个公元前6世纪,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仍然是那些世家大族,平民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贵族的追随者。公民大会的权威,此时也许不过是选举官员、通过决议,是否有对决议的讨论权,不无疑问。[8]然而,这种等级式的优良秩序,也许符合梭伦本人的认识,在公元前6世纪初,也许足够革命,尤其是它允许最低等级的公民参与到城邦政治进程之中,并采取措施确保了社会下层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9]却不适应后来雅典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不能不仰赖平民的支持,并对平民做出不同程度的让步,由此将平民引入政治,逐渐激发出了平民自身的政治意识。[10]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平民基本的生计,为平民参与政治创造了经济前提。于是,到公元前6世纪末,当僭主政治垮台之时,梭伦式的优良秩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更能表现平民意愿的平等(伊索诺米亚[isonomia]),雅典的政体,也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成为民主政治。 平等成为政治要求 学者们公认,平等一词最初可能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克里斯提尼可能把它作为政治口号,用来赢得公民的支持。[11]它基本的含义,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所有公民共同享有的权利。虽然现存文献中该词最初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末僭主被推翻后的雅典,表达的可能是贵族的感受,但后来被以克里斯提尼为首的民主派接过作为口号,以描述改革后雅典建立的民主政体,但作为一个原生形态而非输入的观念,政治实践很可能早于表达它的术语。从希腊历史上看,它可能首次出现于公元前522年。当年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特斯意外被波斯总督处死,他的继承人迈里安德罗斯打算放弃权力,恢复萨摩斯人的自由。他首先为自由之神宙斯修建一座祭坛,然后召集萨摩斯人全体公民的大会。他在会上宣布,他很不喜欢之前波利克拉特斯君临一切的作风,而希望与“你们分享所有权威,并且宣布平等”,作为回报,他只需要得到已故僭主财产中的6塔兰特黄金和自由之神宙斯的祭司职位。这里所说的平等,就是伊索诺米亚。[12]从上下文看,它确实表示所有公民平等享有进行统治的权利。不过,这次试验以失败告终,一者,迈里安德罗斯宣布的平等仍不够平等,他本人希望拥有的6塔兰特黄金与宙斯的祭司职位,固然不足以让他成为僭主,但无疑会使他成为特权分子。二者更加重要:萨摩斯人中部分人反对,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于是迈里安德罗斯被迫放弃了他的主张,转而企图建立僭主政治。经过一系列动荡后,该岛最终被波斯征服。希罗多德言及此处,特别评论了一句,“看来,他们(萨摩斯人)并不是希望自由的。”[13] 尽管如此,权利平等仍是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邦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可能在萨摩斯之前,北非的希腊人殖民城市库列涅发生过一次改革。当时库列涅因王位继承和不同集团的居民之间发生冲突,门丁尼亚的戴摩纳凯斯应邀调处。他的具体做法,多少也有些平等的味道,将原来国王享有的权威大部剥夺并交给公民(只保留了某些领地和祭司职务),并根据库列涅的情况,将它的居民重新划分为三个部落,让公民大会掌握了主要权力,亚里士多德因此将那时的库列涅政体视为与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建立的类似的民主政治。只是因为国王仍保留某些特权,难称真正的平等。[14]如在萨摩斯一样,这种体制大概维持了一代人后被颠覆,该城也在经历动荡后,于公元前6世纪末成为波斯的藩属。 同样在该世纪末,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希腊人城市中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公元前513年,随波斯远征西徐亚人的小亚细亚希腊人僭主讨论是否接受西徐亚人的建议,放弃他们为波斯人守卫的多瑙河上的浮桥自行返回自己的城邦。雅典人米尔提阿德斯发言认可,但米利都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表示反对,理由就是“他们今日之所以各自成为自己城邦的僭主,正是由于大流士的力量。如果大流士的权势被推翻的话,他们便再也不能进行统治了,不拘是他在米利都还是他们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会如此,因为那时所有城邦都会选择民主政治,不会选择僭主政治了。”[15]希罗多德这里直接使用了民主政治(demokrate)一词,[16]很可能是误用了公元前5世纪的术语,更准确的说法,也许应当是平等,因为在第5卷中,当希罗多德提到阿利斯塔哥拉斯为争取米利都人支持反叛波斯的起义时,说的是后者“故意放弃了他的僭主地位并使米利都的人们获得平等的权利”,而米利都人欣然接受。这里所使用的“平等的权利”,就是伊索诺米亚。[17] 相对于希腊世界的上千个城邦,上述事例似乎并不算多。但它至少表明,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的某些地区,确实出现了公民追求政治平等的一般趋势。我们不应忘记,希斯提埃伊欧斯的话代表了亚洲希腊人的一般取向,希腊人对阿利斯塔哥拉斯的支持,则成为那里的希腊人确实向往平等的有力证据。在库列涅,具体负责设计改革措施的是来自阿卡狄亚城邦门丁尼亚的普通公民戴摩纳凯斯。那意味着即使在阿卡狄亚那样相对后进的地区,人们也熟悉这样的概念。而他在库列涅并无强制手段,其措施却能得到库列涅的支持,并且能够维持若干时日,似乎暗示库列涅人也不是完全不认同这样的做法。然而如前所述,这样的趋势在其他地方或者未能完全实现(如萨摩斯和米利都),或者勉强实现,不免打了折扣,且延续时间不长(如库列涅和米利都)。只有在雅典,权利平等不但得到实现,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得到巩固,进而发展成古典时代希腊最为典型的民主政治。因此,我们需要对该术语在雅典产生的背景以及它与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关系略做辨析。 克里斯提尼改革与平等 平等一词首次出现于雅典,应当是在雅典僭主被推翻后贵族们在酒会上吟唱的诗歌中。“我会像哈摩尔狄乌斯和阿里斯托格通一样,头戴桃金娘冠,身负长剑。当时他们杀死了僭主,让雅典获得了平等。”不过因为这句歌词到底出现于何时存在争议,其含义也不免随定年有所变化。人们争议的主要是它到底是首先出现在僭主垮台后的雅典贵族中间,表达贵族的意识形态,即僭主垮台后贵族取得了平等争夺权力的机会,还是出现于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以表达新政体的精神。[18]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它表达的是贵族还是平民的理想,它最初肯定是贵族们创作的,后来被克里斯提尼接受过来,成为了他争取支持的手段,并据此击败了政敌伊萨哥拉斯,在雅典完成了奠定民主政治基础的改革。希罗多德明显认为,平等是克里斯提尼政体的基本精神,并且因此做出了他至今仍非常著名的评论:“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19] 这里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两个,第一,希罗多德将平等与僭主统治对举,显然意在比较克里斯提尼新近在雅典建立的政体和此前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事实上希罗多德曾予雅典僭主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在雅典进行统治时,“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和巧妙的。”[20]不过他仍然认为,在僭主政治下,雅典人觉得自己与奴隶无异,是为主人工作,一旦赢得自由,则自己成为了主人,表现在战场上,就是之前犹如怯懦鬼的雅典人,突然为了保卫民主政治,不惧强敌,一天之内分别击败了底比斯人和卡尔西斯人两支军队的入侵。希罗多德认为,那只能用雅典人享有自由来解释。第二,希罗多德把权利的平等和自由联系起来,暗示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之下缺乏自由,而在权利平等的政体下,享有了自由,因此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公元前6世纪初仍能够接受梭伦等级式优良秩序的雅典人,到公元前6世纪末会主动接受平等的口号,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僭主政治本身的垮台,是贵族争夺权力的结果。虽然修昔底德明确提到,庇西特拉图死后,实际掌握权力的是希庇亚斯。与父亲比较,“他行使权力的方式使人民易于忍受,被他统治而无怨言。事实上这些特别的僭主们长期以来的政策表明他们有高度的原则和智慧。他们对雅典人所征的税不过财产的二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大大地改善了雅典的面貌,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举行了一切正当的宗教祭祀。在其他一切方面,城邦还是依照过去的法律管理,他们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家族中一个成员总是居于公职。”[21]可能正是在修昔底德所说的这个时期,雅典一些著名家族的领袖,如菲拉伊德家族的米尔提阿德斯,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克里斯提尼、卡利阿斯家族的卡利亚德斯等,不管他们过去对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是何种态度,现在都实现了和解,并曾出任执政官。[22]然而,到公元前6世纪末,僭主的统治仍遇到了问题:最为根本的因素,是僭主政治期间普通公民地位的上升和经济地位的改善,要求更多地分享权力,[23]然而如修昔底德所说,在雅典有限的公职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职位经常被僭主家族垄断。同时,僭主打压贵族的传统,尽管在希庇亚斯统治初期可能有所松动,但贵族仍有理由不满,迹象之一,是雅典重要的菲拉伊德家族的一个重要人物曾被暗杀,曾出任执政官的米尔提阿德斯则选择前往色雷斯殖民。[24]从僭主方面来说,长期掌握权力带来的特殊地位,也让他们的行事缺乏节制。希帕库斯对阿里斯托格通和哈摩尔狄乌斯的侵犯,虽然在修昔底德看来不过是爱情事件,好像与政治无关,但引发的后果无疑是政治性的,因为在刺杀发生之后,希庇亚斯立刻解除了公民的武装,并处死了一批可能参与也可能根本与阴谋无关的公民;一些贵族,包括很有影响的克里斯提尼在内,选择流亡国外,更有一些贵族试图借助底比斯和德尔斐的支持,武装返回雅典,推翻僭主政治。[25]僭主政治最后确实是被斯巴达推翻的,但僭主政治垮台的根源,则在雅典国内。 据希罗多德,僭主政治垮台后,雅典最有势力的是两个人,一位是伊萨哥拉斯,另一位是克里斯提尼。两人各自率领自己的追随者争夺权力,但伊萨哥拉斯取得了胜利,当选为公元前508/7年的执政官。克里斯提尼“既然在斗争中处于劣势,便和民众结合到一起去了”,并且赢得了胜利,随后便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在希罗多德看来,克里斯提尼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阿提卡公民进行新的组织,以10个新部落作为主要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单位,把阿提卡的乡村政治化。伊萨哥拉斯转而向斯巴达求助。斯巴达人先发出通牒,要求雅典人流放包括克里斯提尼在内的700家族,随后国王克列奥美涅斯亲率军队到达雅典,意图解散议事会,建立以伊萨哥拉斯为首的300人政权。但雅典人奋起反抗,议事会(不清楚是战神山议事会还是梭伦的四百人议事会)拒绝解散,雅典人民则将斯巴达军队和伊萨哥拉斯围困在卫城中两天,在第三天斯巴达人以非常丢人的条件离开后,雅典人处死了伊萨哥拉斯派的部分成员,请回克里斯提尼,随后再度击败斯巴达组织的三路进攻,并引出了希罗多德那段热情洋溢的评论。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僭主政治垮台初年的政治斗争模式,与公元前6世纪前期雅典政治斗争的一般状况无二: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他们的领袖的率领下,与同样有政治欲望的家族争夺权力。民众最初显然并未完全被包括在内。只是在斗争失败之后,克里斯提尼才“和民众结合到一起”,并且赢得了胜利,随后在民众的支持下进行了部落改革。克里斯提尼之转向民众求助,反映了雅典长期政治斗争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唤起,而克里斯提尼敏锐地意识到了民众如今在政治中的作用。[26]但奥斯瓦尔德正确地指出,是什么让原本在僭主政治下可能得到较多照顾的普通民众转而支持了克里斯提尼?[27]更重要的问题是,克里斯提尼改革实际给予了雅典民众什么实际的利益,以至于他们敢于在克里斯提尼缺席、斯巴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公开发起暴动,将斯巴达人驱逐并将反对派处死?奥伯因此认为,当时雅典发生了一场由人民自主发动的革命,直接后果是确立了民主政治。[28] 这个神奇的东西,可能就是在萨摩斯和伊奥尼亚未能得到实现的平等。虽然希罗多德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克里斯提尼确实借用了这个口号,也没有提供他如何向雅典民众解释他的政纲,但希罗多德的记载确定无疑地表明,他确实向雅典民众承诺了某种东西,并因此赢得了雅典民众的信任与拥戴。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似乎更加明确,“僭主政治推翻之后,进入一段党争的时期,一方领袖是忒珊得耳之子伊萨哥拉斯,另一方是克里斯提尼,他属于阿尔克迈翁家族。克里斯提尼被小集团击败,就提议将政府交给民众,以争取人民的援助。”[29]两人都非常明确,克里斯提尼最初按照传统模式,利用贵族斗争中惯用的小集团(hetairoi)争夺政权,在失败之后才转向民众。他之能够赢得民众支持,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因为他驱逐了僭主,而伊萨哥拉斯是僭主的朋友,但在我们看来,克里斯提尼的成功,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把政权交给人民。[30]不过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具体实施,是在雅典人击败斯巴达干涉军、并召回克里斯提尼及其他流亡者之后。亚里士多德接着补充说,“现在人民已经控制政体,克里斯提尼是他们的领袖”。[31]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原则,是随着新部落制度创立而产生的平等。 克里斯提尼的新部落彻底打破了阿提卡原有的部落格局,它由阿提卡三个大区即城区、海岸和山地各一个三一区组成,三一区的基础是阿提卡原有的德莫(一译村社)。据说这些三一区是根据抽签被随意指定给相关部落的,同一个部落的三个三一区可能相距甚远,但各个部落的中心应当都是雅典城。亚里士多德说,通过这样的组合,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无论大家是来自山地和海岸,还是来自城区,最终都是雅典人,在同一个部落团队中战斗,在议事会同一个主席团中任职,可能还会举行相关选举。此举目标意在削弱地方贵族的影响,增强雅典国家的统一性,但亚里士多德提到,克里斯提尼如此设计的目的,是“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32]这句话令人费解,它既可能指新入籍的公民有资格借此参与雅典政治,也可能指原有公民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管理,即参与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说,后者更为可能。因为通过新部落的设计,以及部落与议事会、公民大会的关联,此后无论是阿提卡哪个地区的公民,尤其是那些距离雅典较远的山地和海岸两个地区,也都能够参与到对国家的管理之中,因此让雅典政治具有了平等意蕴。因为雅典军队以部落为单位组织,将军最初是每个部落一名;议事会主席团以部落为单位,具有重要职责。准此而论,部落确实让民众对政府的参与更加平等。此外,部落和三一区的基础是德莫,它设德莫长,主要责任是登记公民,选举基层官员和处理本德莫的相关事务,从而取代了雅典原由贵族控制的胞族登记公民的职责。议事会议员的选举等,可能也以德莫为单位进行。默里关于德莫在雅典基层创立民主的论断,应当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33]经过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即公民获得的“政治在场性”,不仅在地域意义上,而且在阶层意义上,都更加广泛。“他们既可以通过公民大会直接参与政治,也能经由议事会间接享有政治权利,非但如此,由于广大公民可以对政治事务加以关注,并使自己的意愿在其中得以体现,因此他们也通过委托而享有了权利。”[34]以德莫为基层单位、以三一区和部落为基础组成的新的雅典国家,让“所有公民,无论新老,都在他新的德莫和部落中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克里斯提尼的平等,同时也是他对雅典“最重大的贡献”,正在这里。[35]用平等来形容克里斯提尼新的政体,恰如其分。 克里斯提尼改革本身,可能就是公民平等的产物。与此前的梭伦等人不同,克里斯提尼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取得优势,并且以人民领袖的身份领导改革。从亚里士多德的行文看,克里斯提尼改革是在雅典人驱逐斯巴达人并且召回流亡者的情况下进行的。奥斯瓦尔德正确地推测,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措施,很可能不是以立法家梭伦那样的身份颁布的法典,而是首先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建议、并且经过公民大会批准得以实施的。它的出台和得到实施本身,就是公民平等的产物。[36]虽然雅典民众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克里斯提尼如此复杂设计的用意及其作用,[37]也无法预测它后来的发展,但雅典人愿意接受平等(不像萨摩斯人那样拒绝),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经过公元前6世纪政治斗争的历练,已经具有了参与和掌管国家的能力。雅典人民在关键时刻的政治主动性,与克里斯提尼设计的“十进位制民主”的结合,成为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08/7年那个特定时刻诞生的基本前提。[38] 克里斯提尼的平等,还体现在随着10个新部落创立产生的一系列制度上。议事会从梭伦时代的400人扩大到500人,让更多的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毕竟议事会承担着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主持公民大会、执行公民大会决议、接待外来使节、处理国家日常事务与监督官员等诸多重要责任,是雅典民主政治下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39]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公民不过3万人左右,如果10年轮换下来,则雅典公民中有近20%的人参与过国家机密。随后,10名权力平等的将军组成的委员会,成为雅典主要的军事将领。陶片放逐法则在雅典国家缺少近代官僚体系的情况下,把有关国家政策走向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公民。它一方面让雅典公民成为相关争议的最终裁决者,另一方面,弱化了政治家之间面对面的冲突,有利于维护雅典国家与政策的相对稳定。因此,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政体,普通公民真正开始在政治中发挥作用。雅典人不仅在法律上赢得了平等的权利,而且有渠道和机会行使他们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声称,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政体“比梭伦政体要民主得多”,[40]不过这种政体当时并不叫民主,而叫平等。“与‘优良秩序’相反,现今存在的是‘平等的秩序’”。[41] 与梭伦等人的优良秩序比较,平等的秩序不仅抛开了等级制,它“通过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维护着法律的统治和责任政府”,而且设计了一系列制度,以确保平等的实现,不再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制度不公正的梭伦和赫西奥德那样,把优良秩序的维持单纯寄托于道德。此前希腊人担心的贵族、僭主等统治者傲慢和过分的问题,只有“在遭遇同胞们平等权利遏制的情形下,让其置于法律的判决之下,才能在合法统治的公正限度内,被平等的遏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即政治权力的平等分配,才能确保一个负责的,同时也是守法的政府”,寡头政府、僭主政治等所以傲慢、不守法度,也正是因为它们那里的民众缺乏平等的权利。[42]因此,平等让希腊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政府是否守法与民众是否拥有平等权利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克里斯提尼改革,从制度上确保了这种平等的实现。对于希腊政治思想的发展,平等的权利和制度的保障从此被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此后希腊乃至西方政治思想中,权利、制度设计与国家治理优劣之间的关系,成为他们讨论中最为重要的议题。 从平等到民主政治,不过一步的距离。按照希腊语的定义,民主政治(demokratia)的本意,正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这个词大概首次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希罗多德对它已经相当熟悉,而且有时把平等与民主政治互换使用。[43]不少学者将该词的出现与公元前5世纪中期厄菲阿尔特改革或公元前5世纪雅典海军的强大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平民阶级成为雅典军队的主力,才造就了雅典平民在公元前5世纪的强势,通过阶级斗争和改革,直接掌握了国家权力,并用更加强势的“民主政治”一词,取代了行之已久的“平等秩序”。[44]民主政治执行的政策,也体现了相对贫困的公民阶层对富有者的胜利,并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引起雅典精英阶级的反击。[45]然而,过分强调穷人尤其是第四等级公民的作用,不免有模糊雅典民主本为雅典整个公民阶层的民主的危险。从根本上说,公元前5到前4世纪雅典国家的主要政策,是得到大多数公民认同的结果。而从雅典政策中得益的,也不只是雅典的穷人。[46]在希腊语中,demos一词本身就有代表全体公民的意思。更准确的表述也许应当是,在民主政治下,相对贫穷的公民的权利,较之在平等政体或者有某些民主成分的政体之下,得到了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其利益相应得到了更多的保护,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一定会侵犯富人的利益。
作者简介:晏绍祥,1962—,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已出版的著作有《荷马社会研究》、《希腊史研究入门》、《古典历史研究史》等。
[1] Victor Ehrenberg, Aspects of the Ancient World: Essays and Review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6, p. 79. [2] 在《Eunomia:梭伦的理想政制》(《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中,张巍对此有深入讨论。他以梭伦的诗歌《致城邦》为基础,结合古风时代希腊思想的发展,准确界定了梭伦理想政制的特征及其思想文化渊源。它“体现了‘分配性正义’的城邦政制秩序”,“实现了心智秩序与理想政治秩序的结合”。 [3] Gregory Vlastos, “Solonian Justice”,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xli, No. 2 (April 1946), pp. 69. [4]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 of Greek Culture, vol. 1, translated by Gilbert Highe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5, pp. 136-149. 梭伦一章的标题就是《梭伦:雅典政治文化的创造者》。 [5] 弗拉斯托斯对梭伦正义观和自由观的分析,正以此为出发点,见Gregory Vlastos, “Solonian Justice”, pp. 65-75。 [6]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158页。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5页。 [8] 例如在投票给予庇西特拉图私人卫队时,希罗多德不曾提到进行任何讨论。庇西特拉图之夺取权力和两次被驱逐,也不曾经过公民大会,他权力的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其他贵族家族的关系。见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上册,第27-30页。 [9] 圣克鲁瓦强调梭伦取消债务措施的革命性质,特别指出取消债务为其他希腊城邦所无。但笔者必须指出,赋予社会下层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至少像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一样具有革命性。见G. E. M. de Ste. Croix, The Class Struggle of Ancient Greek World to the Arbian Conquest, London: Duckworth, 1983, pp. 137, 282。 [10] 不少学者倾向于强调雅典政治斗争的贵族性质,但因为雅典国家的特性和梭伦以来平民对政治的参与,平民逐渐成为贵族争夺政治权力中最为重要的筹码。有关贵族争权与民众参与及其与民主政治产生的关系,见陈莹:《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第115-125页。 [11] Victor Ehrenberg, Aspects of the Ancient World, pp. 89-91; Gregory Vlastos, “Isonomia”,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74, No. 4 (1953), pp. 339-341. 如果从年代上推算,平等一词本出现于波斯7个贵族讨论波斯应当采用何种政体之时。但那样一场讨论,尽管希罗多德信誓旦旦地表示确曾发生,然而讨论中使用的话语,表明那只能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或者希腊其他城邦的情景,因此下文的讨论中对此略而不论。 [12]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vol. II,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176-177. [13]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258页。 [14]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329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22页。 [15]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318页。 [16]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vol. II, p. 338. [17]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vol. III,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0. [18] Gregory Vlastos, “Isonomia”, pp. 340-344; Victor Ehrenberg, Aspects of the Ancient World, pp. 89-91. [19]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79页。 [20]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27页。 [2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18页。 [22] 查尔斯·福尔那拉:《希腊罗马史料集》(一):古风时代至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23] 廖学盛:《廖学盛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24]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416-417,444-445页。 [25]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71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第519-522页。 [26] 陈莹:“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第120-125页。 [27] Martin Ostwald, Nomo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9, pp. 147-149. [28] Kurt A. Raaflaub, Josiah Ober and Robert W. Wallac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83-104. [29]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页,并请见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Eudemian Ethics, Virtues and Vices,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0-61. [30] 克里斯提尼的主观动机到底是真心为雅典人创立民主政治,还是有他个人的精明算计,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前者可以埃伦伯格为代表,后者可以刘易斯、西利和希格内特为代表。这里着重讨论他的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个人动机这类复杂的问题,似乎并不重要。见Victor Ehrenberg, Polis und Imperium, Zurich und Stuttgart: Artemis Verlage, 1965, pp. 282-297; D. M. Lewis, 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edited by P. J. Rh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7-98; Charles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Century B. C.,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2, pp. 124 ff.。 [31]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4页。 [3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5页。 [33] 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6-267页。 [34] 梅耶:《古希腊政治的起源》,王师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125页。 [35] D. M. Lewis, “Cleisthenes and Attika”, Historia, vol. 12 (1963), p. 39. [36] Martin Ostwald, Nomo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 p. 157. [37] 默里:《早期希腊》,第269页。 [38] 这里无意否认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而且过于强调克里斯提尼的革命,可能有误读历史、落入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牢笼的嫌疑。但就平等而论,似乎有理由做出这样的论断。黄洋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讨论,见黄洋著:《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125页;《“雅典革命”论与古典雅典政制的建构》,《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39] 有关议事会权力最充分的讨论仍是P. J. Rhodes, The Athenian Boul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pp. 49 ff。 [4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页。 [41] 默里:《早期希腊》,第269页。 [42] Gregory Vlastos, “Isonomia”, pp. 358-360. [43] Victor Ehrenberg, Polis und Imperium, pp. 264-297. [44] 如威廉·弗格逊:《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1-42页;默里:《早期希腊》,第269页;Kurt Raaflaub, Josiah Ober and Robert W. Wallac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pp. 105-154。并请见Robin Osborne, “When was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 ”, in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 eds., Rethinking Revolutions through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28。 [45]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1页;黄洋:《“雅典革命”论与古典雅典政制的建构》,第164-175页。 [46] 芬利已经意识到,雅典富人从雅典帝国的统治中获得了更大收益,见M.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1, pp. 41-61。 |
 首页
首页